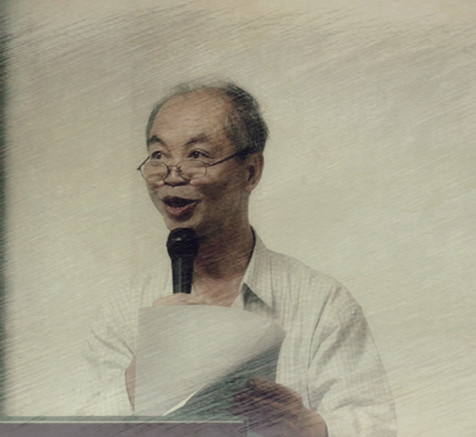
王曉明教授生於1955年,屬於標準的文革世代。文革發生時,他正讀小學四年級。1972年中學畢業,但中間幾年其實很少有機會在教室好好學習,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是在「街道、車間和農田裡」「讀書」的。中學畢業後,他下工廠當鉗工,一直到文革結束。1977年恢復高考,考進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第二年招收研究生,隨即轉讀中國現代文學碩士,198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
由於文革的影響,大陸已經有十年時間沒有培養研究人材,因此,1978年之後招收的前幾屆研究生,畢業後不久就成為大陸學術界的中堅,然後也順理成章的成為各學科的帶頭人。因此,很久以前我就知道王曉明教授是上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鎮」之一。
我所以把王曉明教授這個年齡層的人稱之為「標準」的文革世代,是因為1978年以後招收的研究生年齡極為參差,有的人生於三O年代末期,已經年屆四十,有的人生於四O年代中後期,已經超過三十歲了。如果是生於五O年代中期,那麼,文革結束時也不過二十出頭,差不多等於大學畢業的年齡,在這個時候念研究所,可謂適逢其時,時間上沒有受到擔擱,王曉明教授就是這一類型的人。
改革開放的八O年代,由於對文革極左思潮的反彈,知識界普遍傾向於美國式的自由、民主,文革世代也不例外。譬如,比王曉明大兩歲的蔡翔就曾坦誠說過:
我們把現代化,包括把市場經濟理解為一種解放的力量,理解為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實現保證。
九O年代當我能大量購買大陸圖書時,我常常看到類似的議論,不免為大陸知識分子的「天真」而感到驚訝,最後感到不耐煩,以致於完全不看他們討論中國現狀的著作。那時候我不知怎麼搞的,也把王曉明列為上海自由派的代表,雖然買了他的兩、三本著作,卻很少讀。後來有一天,跟陳光興談起王曉明,因陳光興跟王曉明已有多次交往,他跟我說,王曉明絕對不是一個自由派,你不應該有這種偏見。後來,我跟王曉明的學生薛毅有較多的交往,發現薛毅最少也可以算是新左派,再跟他問起王曉明,他跟我說,王老師的思想已經有了轉變,現在已經不是自由派了。有一次我見到他本人,跟他談起思想改變的事,他說,我怎麼能不變呢?我不變,我的學生也要逼我變。我沒想到他這麼坦率,從此對他有了好感。
我請王曉明教授編一本選集,在台灣出版,他最後決定只選近十年的文章。這樣的選集雖然不能看出他思想轉變的歷程,卻能更清楚的看到他在最近幾年集中思考的問題。我一篇一篇的讀著這些文章,常常為他的真誠而感動。他毫不逃避的面對當今大陸所有其亂如麻的諸多問題,他不相信美國式的自由經濟和民主制度能解決這些問題,他也拒絕回到五O年代至七O年代的左傾路線。這樣,他就只好徹底擺脫既有的主義與思想,從沒有立足之地重新探索。他把自己的這種立場,借用魯迅的說法,形容為「橫站」。這就是說,不採取單執一面的思想來批判,如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這樣的思考方式非常無力。有些人為了回避這種困境,只好把言說弄得非常複雜,其實是閃爍其詞,不著邊際,沒有直面問題。這還不如「乾脆跳出泥潭,直截了當,怎麼想就怎麼說,雖然粗暴、簡單,卻能夠撥開迷霧,擊中要害。」這樣的結果,就會惹來秉持各種「主義」來自不同方向的攻擊,於是,你只好「橫站」,以便隨時面對四面八方的敵人。
這樣的探索既需勇氣,還要把持著不掉入虛無之中,其實是非常痛苦的。讀過魯迅的人都知道,這是魯迅的作戰方法,這需要堅強的毅力,和對無法預知的理想的堅持。這只能在茫茫的黑暗中,努力護持著一盞嚮往著「善」的微弱的燈火。這也是魯迅給予人的最大的支持與撫慰。
但我們也知道,魯迅的時代距離現在至少七十年以上,現在的中國畢竟已經不是魯迅時代的中國。雖然現在的中國讓我們大惑不解,但卻沒有哪一個國家敢再派軍隊侵入;而且,中國再怎麼貧富不均,大概也沒有人會餓死;即使發生天大的災害,如川陝甘大地震,中國至少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最大的人力、物力迅速搶救,這都是一九三O年代的中國夢想不到的。我們也知道,這是經過七十多年的磨難,以千千萬萬人的犧牲與奉獻所換得的。雖然代價極為慘重,但也不能不說是一種成就,這恐怕是很難否認的。
其次,我們大致也可以肯定的說,中國目前所面臨的種種問題,是不能用西方式的自由市場和民主體制來加以解決的。譬如,要是把土地私有化,可以自由買賣,不但沿海城市的房子很少人買得起,而且,廣大的西北地區和農村地區會越來越少人居住。難以想像,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中國人口全部集中在沿海的城市,中國會變成什麼樣子。又譬如,像大陸這樣各民族雜居的情況,如果按台灣的方法舉行各種地方選舉,也按台灣的選舉那樣訴諸族群矛盾,能夠想像大陸會不鬧亂子?中國不能亦步亦趨的走西方道路,除了越來越少的僵硬的自由派之外,大概也可以算是大多數人的「共識」了吧?
最後一點,最近二十年的經驗,也很難不讓人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價值體系大起懷疑。如果他們真的是講究人權,難道他們就可以為了幾個「流氓」,進而肆無忌彈的轟炸阿富汗、伊拉克、南斯拉夫、利比亞,炸死許許多多無辜的平民,這也是為了維護人權,誰相信呢?美國金融出了問題,負債累累,既無力改善,也無力還債,就不負責任的大印鈔票,把問題丟到別人身上,這叫自由經濟,誰服氣呢?
再說遠一點,憑仗著優勢的航海技術與武器,走遍全世界各地,到任何地方,殺人搶土地,掠奪物資,還把千千萬萬的人掠賣為奴隸,並聲稱這是西方文明的偉大成就,那麼,所謂文明也不過是赤裸裸的「強淩弱」的代名詞。所謂個人主義的成就,不就是有能力的個人的集合到處殺人越貨所獲得的大批的戰利品嗎?在人類史上,以戰爭決勝負確實是人的生存法則之一,但像西方文明這樣強調「唯強為尊」的,恐怕當數文明史上的特例。
再說,當西方還遠遠落後於伊斯蘭國家、印度和中國時,他們可以隨意的學習、吸收這些地區先進的技術,而這些地區從來也就沒有知識產權的觀念,從來就沒有想到跟西方人要權利金;現在反過來,當西方人統治全世界時,他們的每一種新發明、新技術都嚴加保護,並且要付上極大的代價,才能用上這些技術,買到這些產品。人類文明的成就本來是互相流通的,而西方人卻以為真正的文明只有他們才能創造出來,你要這種文明,就需要跟它「購買」,這大概就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偉大成就吧。這樣的文明理念,我們可以再相信嗎?
再進一層推論:假如我們相信這種文明理念,並且假如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的一等強國,我們可以像美國人那樣,享用全世界最大的財富嗎?美國只有兩億多的人口,而中國卻有十三億,如果將來中國的每一個人,都要像現在的美國人那樣的消費,你能想像中國人要耗費多少世界資源?二十多年前,不懷好意的西方人還常常說,中國人要吃光世界的糧食,就是按照他們消費的邏輯推論出來的,因為兩、三百年來他們就是這樣「啃光」世界的最大資源的。這種資本主義的邏輯,不能在中國強大後由中國繼續推行下去,是誰都一眼看得清楚的。因此,西方這種建立在儘可能滿足人的慾望之上的經濟邏輯,絕對不是人類文明的持盈保泰之道。
所以中國現在的發展問題,不只是中國本身的問題,而是人類的文明是否繼續維持得下去的問題。王曉明教授說,中國人現在還感受到,「那種難以把握國家和個人命運的茫然的神態,甚至那種不遠處正有巨大的動盪向我們逼來的不詳的預感」,我覺得正是中國被捲進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以後中國人所感受到的普及全人類的危機感。因為,中國如果也按照這個邏輯發展下去,那就不只是中國毀滅,人類文明也會跟著毀滅。中國的崛起正碰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歧路口,更正確的說,中國的崛起也許可以改變西方資本主義那種霸道文明橫行全世界的局面,從而將人類引導向另一種文明方向,這就是中國發展問題的複雜性。
王曉明教授是深切了解這些的,這從本書的第二部份「中國革命的思想遺產」中的各篇文章可以清楚的看出來。這些文章談論的是中國現代早期的思想家,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人,在面對西方列強的侵逼時,如何思考中國以及人類的前途問題。這些人在思考中國人如何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出人意料的視野開闊,讓我們感到驚訝,似乎預見式的為我們提供了現在應該思考的方向。以下我想引述王教授從中得出的最核心的看法:
1.眼睛是這樣地望著世界,當規劃未來中國的強盛藍圖的時候,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就特別警惕霸權式的「強國」欲望和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幾乎每次展開這一類的論述,這些思想家都要提到「被壓迫者」的身份和記憶,要大家躬身自問,過去和現在,我們中國/漢族人是怎麼被壓迫的!正是這樣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常人心理,成了他們舉出的最大理由。確實,一個始終記著自己如何因為力弱而遭遇欺淩的人,不大可能理直氣壯地想像將來揮著粗大的胳膊去欺負別人。
2.在這樣的視野裡,「解放」不會凝固在某一個層面,總是會往更為宏觀和微觀的方向擴展,壓迫和被壓迫的角色,也因此可能甚至必然互換,或者一身兼二任,一面承受強者的壓迫,一面也壓迫更弱者,借用章太炎的話來說,是一面為真,一面為幻。不用說,這樣的總是從變動和辯證的角度來理解革命目標的思路,是比後起的那些單向尊奉被壓迫者的理論,更能表現這一時期中國思想的被壓迫者立場的強固:它不但具備譬如佛學式的世界無邊、眾生平等的寬闊情懷,更有一種從切身感悟中生長出來的反省之心:昔日傲然自居為天下中心,現在卻整體上居於劣勢,被洋夷倭寇壓迫得抬不起頭,從這樣的經驗起點走出來的思想,怎麼可能止步於「彼可取而代之」式的健忘與狂妄?
看到這樣的話,我不禁為晚清思想家的博大與深微而嘆服,並且佩服王教授從他們那裡找到了克服西方資本主義邏輯的最大支點。
除了孫中山的「濟弱扶傾」之外,我以前很少注意到中國早期現代思想家在這方面的看法。當我考慮中國強大以後會如何面對世界時,我總是想起古代的漢族和周邊的少數民族是如何由衝突而和平相處而相融為一的過程,我也常想起古人所說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然古代的中國都知道不要強迫「蠻夷」服從你,那麼近代淪為弱勢者、將來再成為強者的中國人,更不應該以強者的姿態去屈服別人。看來,這樣的想法,中國早期現代思想家不但已經想到,而且已經想得很周到很深刻了。
令人感慨的是,民國建立以後,由於國勢日危,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喪失了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胸襟,變得一無所有,甚至自鄙自賤,認為只有跟著人家亦步亦趨,才能自我解救。自由主義的西化派不用說了,甚至社會主義革命派都有這種傾向。最近十年來,我突然領悟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革命論,也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它對於「進步」的盲目信仰,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的科學規劃,都是西方的產物,和中國一向的文化並不是同質的。譬如說,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如「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說的是一種天下為公的精神,而並沒有訴諸於嚴密的制度設計,因而顯得更富於人性。
王教授把中國的現代分成三個階段: 一、1880─90年代到1940─50年代;二、1940─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三、1990年代以後,我覺得有相當的道理。1990年代以後,中國不但從綜合國力的增長上得到自信,而且在思想上終於逐漸擺脫五四以後唯西方是尚的傾向,開始回歸中華文化,並且想要從中華文化之中尋找克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途徑。回歸的方法之一,就是像王教授這樣,從中國早期現代的思想家中去尋找靈感──因為他們還有傳統文化的底子,還沒有喪失對傳統文化的信心,在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時,還有「對峙」的雄心。現在我終於了解,最近二十年來大陸學界的晚清熱是有道理的,因為,經由這一條途徑,最容易反思傳統。
再度回到傳統來尋找未來中國、甚至全人類的出路,這樣的思想傾向,在大陸已經相當普遍,而且,遍及各個世代的知識分子。從1940年代中後期出生的那一代算起,以後每十年算一個世代,至少在我認識的人中,一直普及到1970年代出生的人。所以我認為,現在這種探索雖然還十分艱難,雖然還是「橫站」,雖然還不能說有一堵牆作後盾,但至少總還有兩、三個可以憑靠的支點,這是不用懷疑的。我看了王曉明教授這本書的許多文章以後,越發有這個信心。
2013/2/2
《横站——王晓明选集》2013年2月人间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