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中学时我们每年都会参加投票选班长,但十八岁成人后,投票这个行为就变得稀缺且无意义。无法参与政治,我们可以全身心的参与赚钱。在市场领域,我们的参与感绝对不比欧美人差。不论是吃饭、看病、买房、投资,还是为自己找工作、为子女找学校,每件事都像打游戏:惊险、刺激、竞争激烈,有些基本规则、但又充满偶然性,需要技能、耐心、与冒险精神,给人以强烈的参与欲与存在感。如果我们只想改造私人生活世界,只想参与资本市场与物质生产,我们拥有广泛、真实的参与权利和自由。
但我们无法永远做宅男宅女。跨出私人生活世界,进入公共空间,我们的参与感顿时受挫。去年秋天我随朋友到浙江椒江的一个村庄,村民生活富庶,一百多户人家拥有两百多辆车,但村里到处都是垃圾,村边的小溪臭气熏天。维系村庄公共生活的机制已经瓦解殆尽。[1] 为什么大家没有一起努力把村子收拾干净?是什么导致大家在公共生活世界变得如此冷漠和无力?
上世纪中叶的公有制改造是一个国家化的过程,而非公共化的过程。我们的生活世界被一个金字塔状的国家行政体系管理起来,而开放参与、平等讨论等公共机制却没有得到思想上的呵护和制度上的保障。我们有“公家”,却没有“公共”。“公家”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政府:代表公家的是实体化的领导,而非动态的公共机制。文革的所谓“大民主”实验以国家力、个人崇拜、青春期躁动为动力,进一步摧毁公共机制。改革开放后,私人生活世界逐渐从金字塔中释放出来,但公共生活世界依然是“公家”的领地。同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被简化为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再进一步被量化为个人收入和 GDP 增长。因此,从“公家”到私人的关注都局限于创造经济价值;生活的其他方面退居其次,甚至被完全忽视。“私有”不再是被批判的观念,而被看做是高效的方法。行政系统的集权进一步加剧,委员会制被一把手负责制取代,“公家”的私人色彩越来越浓。
我们大多习惯了这样的现实:公共生活归“公家”管。“管”这个字有两层意思:治理与负责。既然我被你管(治理),那你就要管我(负责)。既然我不能管(治理),我也就不管了(负责)。污染了空气、河流、土地,只要不被罚款、不被曝光、不成为热点新闻,其他人也不会来管“闲事”。“公家”也乐见大家不管,因为这样就不会出现七嘴八舌、争执不下的情况,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可以保证高效。不少人都抱持这样的观点:过往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正是因为精英集权的高效。
我和大部分国人一样,对自己生活的社区、城市、国家并不了解,也从未将茶余饭后的闲谈和网络空间的阔论转化为对公共生活世界的切实关注。能否在小区内限制车速以免撞伤老人和小孩?是否应该禁止地方电视台使用方言?如何改善我们这座城市的空气?怎样才能让经济增长率(g)超越资本回报率(i)从而逆转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2] 我不了解公共财政,也不知道如何发言,更不知道我的意见能改变什么。[3] 久而久之,我习惯了不再去关注那些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和周围的朋友一样,安心享受幼儿园的无忧无虑,让大人们去操心大人们的事儿,直到有一天我听说家门口要兴建日处理三千吨垃圾的焚烧厂。
2
反观自己,我才意识到《每个人的东湖》是多么难得。
东湖是武汉市区最大的湖泊,面积约是杭州西湖的六倍。2010 年 3 月某媒体报道,武汉市政府将东湖北岸 3167 亩土地以 43 亿元的价格卖给一家房地产集团,用来兴建主题游乐园、度假酒店、商场和高端住宅。此事存在诸多争议:原本用来为市政项目筹集资金的土地以低价卖给了房地产集团;近 2000亩土地位于东湖风景区内;东湖渔场的 450 亩水面将被填掉。[4] 交易披露后引起公众关注。地产集团立刻动员专家和媒体资源,宣称其开发项目环保、生态,将为武汉创造新的旅游资源和休闲设施。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严密控制媒体,将事件列入敏感词,网络空间的讨论也被封锁。
在此情境下,武汉艺术家李巨川(1964 年生)和李郁(1973 年生)决定发起一个名为《每个人的东湖》的艺术计划,邀请普通市民以艺术的方式来发出声音,表达关切。他们在邀请书中写道:“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仅仅是,今天尚留有许多我们可以接近的湖岸和水面,暂没有成为少数人的领地,暂不需要购买门票,那么,我们想提出一个建议:让我们立刻去接近这些湖岸和水面吧,也许这是我们自由地享用东湖的最后机会。”[5]
这个艺术计划向所有人开放,参与者可以自由选择东湖沿岸和水面的任何地点进行创作。计划从 2010 年 6 月 25 日开始,到 8 月 25 日结束,两个月间近百人以个人或小组的方式创作了 60 件作品。[6] 参与者以武汉当地的年轻艺术家为主,但也包括朋克乐手、诗人、学者、自由职业者、戏剧工作者,及多位住在其他城市的公民。诸多作品限于个人行为,没有观众:大栓沿湖写生;吴维用两个玻璃罐封存东湖湖水和泥土,待地产项目完工后再将其送回原地;袁晓舫打破平日在室内游泳馆游泳的习惯,到东湖唯一的免费游泳场“东湖武大游泳池”畅游 45 分钟。也有不少作品以群体的方式展开:吴梦(上海民间剧场团体“草台班”的成员)和多位合作者一起在凌波门外的湖中平台上演了戏剧《免费的 XX》;由诗人张先冰、学者张三夕、设计师阮争翔组成的“社会建筑师群”为东湖边的八个丁字路口命名,并举办户外朗诵会,邀请公众和他们一起朗诵与这些路口有关的原创诗歌、散文、调查报告、收费单、行政通知;BMX 小轮车高手刘真宇和十几名玩家一起在凌波门附近水域用木头搭建了一个抛台,组织了“BMX 跳湖游戏”。


BMX 跳湖游戏,2010 年 7 约 18 日,武汉大学凌波门附近水域
李巨川和李郁作为发起者并没有与参与者见面,也没有组织大家聚会,因为他们担心聚会可能引起政府的关注而令项目被静音。他们为项目建立了网站(www.donghu2010.org),通过网络与参与者联系,在网站上及时发布作品的消息和资料。虽然他们认为某些作品做的不够好(“太过小清新”),但他们抱持平等、开放的态度,将自己的角色定义为平台建设者,而非“策展人”。这样的组织方式也构成了一种抵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没有谁是所谓的专家、领导,机制是透明的,权力被转化为分工,每个人都尽自己所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努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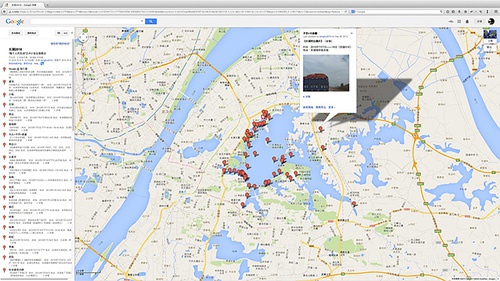
网站用谷歌地图呈现出参与作品的具体位置
《每个人的东湖》不只是试图对地产交易、政府禁言做出些许抵抗,更重要的在于唤起我们对公共生活世界的共同拥有感。东湖属于我们每个人。和生活在村庄的人们相比,住在都市的我们更难对自己所处的公共生活世界产生共同拥有感。毕竟我只是千万分之一,无法感受到一个偌大的东湖到底和我的生活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我们生活在大规模的复杂系统中,某些阶层更利用权力和资本将系统的核心机制遮蔽起来。我们只有付出努力,才能抖掉冷漠,看到本就属于我们的公共世界。发起者邀请我们做的不是“签名表示支持”那样简单的参与,而是要我们发挥想象,用身体去开拓空间,感受到自己与东湖切身的联系。
3
上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木刻运动是艺术介入现代中国政治的发端。此前,书画的创作、观赏、流通仅限于文人阶层,虽然不乏与政治相关的情感和符号,但并不构成社会变革的政治动力。木刻运动采用可以复制的媒介,推崇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风格,关注时政和底层民众生活,建立开放的合作型创作机制,致力于公共展览与传播。[7] 这一系列根本性变革使得木刻运动能在很短时间内将蔡元培开启的美术教育的公共化进一步拓展为艺术创作与传播的公共化,使艺术成为公共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桦,《怒吼吧,中国!》(1935 年)
木刻运动由鲁迅等左翼知识分子推动,成员主要是学生和青年艺术家。他们自发组织各种团体,如 1932 年江丰等人在上海成立“春地美术研究所”(成员包括留法归来的艾青)、1933 年国立杭州艺专同学组建“木铃木刻研究会”、1934 年李桦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发起“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等。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政治理念,但木刻运动初期具有强烈的自发、民间色彩,并非政党政治的一部分。
随着民族危机日渐深重,众多年轻艺术家从城市移居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党对文艺的态度和政策日趋强势,因为文艺是“人民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创作”被“文艺工作”取代,党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方法、目的提出了明确要求,文艺有了对错之分。是否思想正确、是否能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动员劳苦大众成了评判作品的首要标准。独立思辨与想象的过程远没有达到宣传目的的结果重要,甚至被认为是反动的。总括来说,三十年代,艺术经历了从文人雅趣到民众运动的转变;从四十年代开始,艺术又经历了从民众运动到政治工具的转变。政治宣传主导艺术的情况从1940年代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参与性艺术”对中国人来讲并不陌生,其历史脉络和现实情境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在西方,“为艺术而艺术”自十九世纪开始就逐渐成为主流艺术观,至今不倒。参与性艺术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环保运动及情境主义、行为艺术的合力推动下,逐渐浮现出来的具有先锋性的艺术形式,虽然近年来在艺术界内部获得诸多关注和讨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浮现的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更推动其升温,但对大多数西方民众来讲仍属新生事物。在中国则不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在毛时代一直受到批判,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重提,九十年代后在市场的推动下,成为了当下年轻人的主流艺术观。对经历过毛时代和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参与”、“介入”则曾经是艺术的主流。在今天重提这些理念会引发复杂的历史情感:一方面,“参与”具有关注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积极性,和“平等”、“主人翁责任感”等社会主义理念一样令人感到亲切;另一方面,毛时代的“参与”经常带有强迫性,每个人都必须参与政治运动,在某些情境中,参与更和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整风、反右、文革中都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换句话说,二十世纪的历史让“参与”这个概念在中国同时具有社会自发与体制强迫两种截然不同的经验与内涵。因此,参与性艺术在中国面对的阻力,既包括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私人至上和公共冷漠,也包括基于国家主义的集权体制和精英心态,更包括民众因历史伤痛而挥之不去的对政治运动的担忧、甚至厌恶。
区分自我组织的、去暴力的、关注民众的“参与性艺术”──不论是上世纪的木刻运动还是《每个人的东湖》、《民间记忆》等正在发生的实践──与固化为政治工具的、自上而下由政党和国家主导的、需要通过暴力维系的所谓的“革命艺术”[8],至关重要。二十世纪初形成的追求平等、自由、共同美好生活的进步思想是中国参与性艺术的源泉;而改变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冷漠和国家主义造成的恐惧则是参与性艺术最大的挑战。
1930 年代参与木刻运动的年轻艺术家面对的是民族存亡的危机。或许他们对集权制度的妥协是民族存亡关头必须做出的抉择。今天,拥有了温饱和基本民族尊严的我们面对的则是环境、信任、与平等的危机。如果继续依赖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驱动力的政治集权+经济自由模式,如果没有广泛的、自发的参与,我们是否能够避免危机演变为灾难?参与性艺术自身并不能完全改变我们的现状──它需要和其他进步力量形成联结──但参与性艺术作为一个想象空间却弥足珍贵,因为正如王晓明教授所言:当下最大的“反革命”之处是不相信我们能够改变现实,认定我们只能努力去适应现实。
真实并不总是美,但追求真实却是。── 纳丁·戈迪默[9]
注释:
[1]关于乡村公共生活的变化,参见阎云翔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英文版:Yunxiang Yan,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经济学家 Thomas Piketty 在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Belknap, 2014)一书中,通过大量历史数据分析证明,各国贫富差距的恶化主要是因为资本回报率(i)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g),导致富人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超过整体经济的增速。他提出应该征收全球财富税以扭转贫富分化加剧的现实。
[3]由吴君亮创办的中国预算网(http://www.budgetofc
[4]1 亩约等于 0.165 acre。
[5]“每个人的东湖”艺术计划参加者征集, http://www.douban.co
[6]其中两件作品是在 8 月 25 日后完成的。
[7]参见 Xiaobing Tang, Origins of the Chinese Avant-Garde: The Modern Woodcut Mo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8]这样的“革命艺术”实为反革命的。我的这个观点是受到文化研究学者王晓明教授的启发。他指出,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很多实践实为反革命的,包括国家机器对社会的严密控制、改革开放后对“不平等”的全面拥抱、人类中心主义等等。参见 2014 年 1 月王晓明在《汉雅一百》论坛的发言,http://thehousenews.
[9]The truth isn’t always beauty, but the hunger for it is. —— Nadine Gordimer
————————————————————————————————
郑波,香港城市大学创意传媒学院助理教授。
本站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2.5 中国大陆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普陀区白玉路98弄 电话:66135200
沪ICP备17002797号 公安机关备案号:31010702003303
版权所有:庚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