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回城故事
回城故事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6-04-22 04:36:54 阅读:
编者按: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威廉斯曾反复使用感觉结构来描述每一时代生活经验中的共同性,这一概念为文化研究者从理论到实践打开了一条通路,
编者按: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威廉斯曾反复使用“感觉结构”来描述每一时代生活经验中的共同性,这一概念为文化研究者从理论到实践打开了一条通路,而“经验”则因为它自身的丰富性而具备可供深入解读的意义。当代文化研究网特推送两篇经验性的访谈文章,它们属于地方经验,但是因为所在地域——作为“共和国的长子”而走在新中国前列的东北——而具有了普遍性,成为了时代的缩影。在两个被采访者生活经历中,时代变革的大手隐约地推着他们前行。今天,被结构转型抛弃而社会问题重重的东北,在不断地发出抗争的声音。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温共和国的历史,思考看似独立的个体经验之间的血肉联系,反观当下仍有待我们承担的责任。
被访问者:李宝琛,1951年生,曾任哈尔滨市职工大学副校长,已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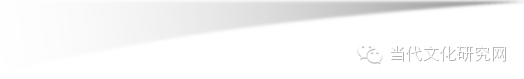 李宝琛,出身于哈尔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祖上是满族镶黄旗,属于清八旗中的上三旗。1968年,他作为成千上万的下乡知青中的普通一员,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某建设兵团在黑龙江省黑河地区的一个马场培育种马。黑河离哈尔滨千里之遥,李宝琛很快就开始为回城做打算。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 27岁的李宝琛已经作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自动仪表专业读到了三年级。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他返城读书的历程尽管有点曲折,但总还是幸运和顺利的。
和我年龄相仿的人,这时候多数是下乡刚回来或者仍然呆在乡下,回城的途径基本上无外参军或招工,能上大学的人微乎其微啊。我这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68年下乡,在生产建设兵团1师11团,在黑河守边疆。那时咱们国家跟苏联关系紧张,我们这叫在“反修前哨”屯垦戍边。响应毛主席号召么,一方面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方面练兵。还是以农为主。我那时候在黑河马场主要负责培育黑河种马,也种地建房、上山伐木,工作还是比较出色。1973年以后开始招工农兵学员,那时我工作环境还不错,也没有什么上学的概念。参加了一次文化测试,因为工作紧张,有经营90多匹种马的任务(当时一匹两年的种马能卖四千八),测试完了也就算了,本来名额就少也没再争取。74、75年社会主要精神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我还代表团里去大寨参观学习。这前后我两次回哈尔滨探亲,第二次回家就感觉形势变化很大。最明显的就是文革的气氛没有了,人的思想也活跃了,都不那么保守了。那时知青返乡、上学的也活跃了、多了。自己感觉单在农村兵团工作不是长久之计。1975年开春我带着种马的血样去长春化验马四号啶,感觉长春那边形势更不一样了,社会风气、人的状态变化都特别大,社会思想好像不是我们当时主张的“扎根边疆”。就这么出来几次之后,感觉在当地就憋不住了,萌生了走的想法。简单的离开回城务工又感觉没意思,当时家里都在兵工厂当工人,回去分配也肯定在机械局,不想去,想当兵,还想上学。当兵的路不同,因为是团里的干部,团里不放就不能走。上学的路是通的,于是我75年就开始准备。
当时上学要经过文化测试、群众推荐,前两条都通过了还得单位保送。文化学习我心里是有底的,73年参加测试也不是很难,说得不好听就是看你认不认识字,加减乘除能不能算明白。我一直没间断学习。平时看马列著作,看毛泽东文集,社会科学书选。还有范文澜版的《论历史唯物主义》。再就是一些业务书,数学,主要是些简单的中学课本。我在团里是干部,除了能看着规定的一报两刊,还可以订《参考消息》、《解放军报》,这在当时可不太容易看到。我们属于部队系列,国内国际变化了解一些。有一些在军队搞情报工作的朋友就就给我讲苏、日军队的状况,当时中苏边境紧张,说苏联24小时可以从远东调7、8个师过来。那距离连飞机都要飞十几个小时,可见人家苏联的技术水平有多高。当时就想,无论是为了报效祖国还是今后自己发展,都要有文化。这就更坚定的想去上学。
后来文化测试语文数学都很简单,“群众推荐”我们一共是63个人。我自己投给自己一票,我就是63票满票第一名。单位一共有三个名额,第一上大学,第二上中专,第三中专预备。我第一就上大学了。第一志愿报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第二志愿是大连海军指挥学校,现在叫大连舰艇学院。虽然志愿报的是这样,海军指挥学校倒是差点先上了。大连海军指挥学校有面试,因为总要出国远洋,要代表国家形象,仪表得端正,歪瓜裂枣的不能要。过来招生的老师待一天就走,他们就先看档案。当时我们这些干部的档案在团里,招生的能看到。很多战士的档案在营里,要一级一级的拿上来根本来不及。能看着的档案也没有多少,还真选上我了,让我当天务必赶到。我们马场距离120华里,我就开着农场的胶轮拖拉机,把斗摘了开车头,一小时能开20多里,赶到了,人家看我各项指标都合格,就是报的第二志愿,问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学校啊。其实我当时主要是想回家,上哈工大就能回哈尔滨了,父母在不远游么。就这样海军学校那边还是告诉我回去准备基本就能上了。可这事儿让陪同的参谋长听去了,他上下一运作,这名额就让他外甥给顶了。这都是后来知道的。6、7月份哈工大的正式通知下来,我就准备上工大了。也没啥遗憾,7年过去总算回家了。
上了大学的李宝琛是被更多的人羡慕的,毕竟与我们在很多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经常见到的轰轰烈烈的返城潮相比,更多的人的命运在这个大转折的时期多少显得有些沉寂,他们似乎总是“沉默的大多数”。而返城的李宝琛也有自己羡慕和钦佩的东西,这也是他喜欢自己的专业——哈工大自动化仪表专业——的理由。
羡慕我的人?那是相当多。我们全团上万人,73年到76年四年走了不过百十来人,77年恢复高考后又走了也不到一百人。多数人后来的去向我和几个出来的几乎都不知道。
上大学,选理科是想干点儿实事儿。在农场搞了很多年机械,农场有的机器都会使。本身也喜欢机械这一行,也羡慕工人。大学里所学专业以前都是直接安排的,也不能自主选择。我学的专业是自动仪表专业。当时对仪表的感觉就是小表,男同志就学个小表好像施展不开,没有机械有意思。等开始学习了发现这仪表可不是“小表”,大的像楼房一样大。仪表老说法叫“热工仪表”,温度、压力、流量,凡是需要仪表测量的元素都需要仪表,现在航天设备也离不开仪表。
刚接触课程的时候跃跃欲试,先学制图、英语、高等数学。我们一个班年龄差别很大,从49年的到57年的,文化水平什么样都有。补数学时从初高中补起,开始还行,越往上越难。学一个学期后就基本把英语放弃了,学不过来。哈工大的教学比较正规,按国家安排有实践环节,三年级专业刚入门,连个正规图工都算不上就下去实习了。先去大庆化工厂、炼油厂,干的活儿是检修测绘仪表,主要是跟老师干,边干活边学习。我们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理论都说不上充实,更谈不上实践。仪表检修测绘还是比当地的工人强,手法上学的东西还是有效果的。在大庆干了三个月觉得学的东西有用,全是我们专业的必须知识。一天弄得跟工人一样,也说不上苦,感觉自己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充实了,挺高兴。之后又去大连仪表厂实习3个月,对理论学习有很大帮助,回头再学习发现数学、物理这些更有用。就彻底放弃英语了。当时我们学樊英川版的《高等数学》还学苏联的。
当时年龄比较大了,入学时24岁,78年毕业就28岁了。当时想一定要好好学习,为自己以后也好,为投身国家建设也好,都要好好学。我们当时都是这个心态。全班都统一起来,利用政治学习时间补课。每周六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我们有同学在门口、楼道把风儿,拿报纸在前面做做样子,没检查的就开始学习。我们把老师请来,门一关,让老师解题,一直到晚上九点,坚持到毕业。工大的老师真都是好老师,特别认真。文革过去了很多被打倒的老师都回到学校,但身体都不行,上一会儿就累了,讲的知识不会错,你问个问题他们有时候反应不过来,文革时候都被打傻了。那时候我们班老师都愿意来,能正经讲课,学生也认真听,能提出问题。我们这些学生年龄都比较大了,多数在农场工作过,基本都抽烟,老师想不起来了我们就给老师点根烟,边抽烟边想,有时候抽一半想起来就马上讲,要是一根烟抽没了就下节课讲,我们有位老师,平时在走廊在食堂在什么地方碰着他了,他马上就给你讲明白。很多老师现在都去世了,很多都对国家有特殊贡献。
1978年,大学毕业的李宝琛被分配到三机部在四川江油的一个研究所。又一次远离家乡,去那个陌生而僻远的地方,如今那个城市因为一次震惊世界的大地震而人所皆知。李宝琛在那里呆了两年,但正是在这里,他慢慢接触到经济转型这个时代命题的枝枝叶叶,也留下了一些属于他自己的美好记忆。
我上学的时候是“戴帽分配”,上学就定了你是给哪儿培养的,毕业就得去。我该去的单位是第三机械部航空工业部。毕业时候政策就变化了,赶上小平同志复出,说现在的毕业生不能浪费。这一个“不能浪费”我就被分配到四川江油624研究所,就是08年四川地震那地方。当时国家政策就是这个政策,要服从分配,虽然比较恋家,让去也就去了。我们就二十几个人,好一些的分配到北京机械局,现在都成了领导干部,还有分配到四川绵竹去搞科研,现在还在那儿,地震都赶上了。
当时还不知道去了让干什么,就想无论让干什么都好好干,结果第二天就被领到操作台前。设备是国家二级、省一级标准。买回来以后就没有人用,这个活是好汉子不愿干,坏汉子干不了的活儿。调整计量标准属于科研二线,后勤保障,不算一线,操作精密设备还不是谁都能干。当时我们去的都是清华、交大、哈工大这些好大学的学生,都在大山里呆着。我就分到这么一个工作,接手后我才知道,由于10年动乱咱国家10年没和国际上调试对标,所有的研究数据都是在标准错误的情况下得出的,都不能用。这时我们所里就比较重视计量标准,靠我的设备校准其他设备。我的设备马上就投入使用了,这就为所节省了一万两千多块钱。之前每个月都得拉着设备去成都校准一次,一次连去带回来最快一星期,我这个设备拿走了其他设备也得停工,这不是误工么。现在,我的设备定期拿到成都或者北京上海校准就行了,不耽误生产。
有没有奖金?肯定是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省了花了都是公家的,我这成果报到所里没人当回事儿。一万二不算多,那时我们地区的研究所一年国家有1600万科研经费,跟现在一两个亿差不多,我这点儿小钱儿,领导没看上。那个时候,四川是三类地区,工资少,大学毕业生一月45块钱,要在哈尔滨能赚66块钱。不过一个人足够了。每天就想着工作,也没别的要求,除了吃饭也没什么花销。个人工资哪能和国家科研经费比啊。
后来又有一个这样的事儿。第二年,我的设备需要一个配套设备,需要去上海买,大概一万八。我当时把计划报到所里,但没敢说多少钱,领导问我,我说挺贵的,大钱。领导就让我回去再各方面考察一下,是不是非买不可。过一段时间又开会,领导就问你那设备到底要不要,多少钱?我各方面都考察了的确是特别需要,不然很多工作都完成不了,就战战兢兢的说要花一万八去上海买,领导二话没说就批准了。我当时特别震惊。后来老人儿告诉我了,十万以上才叫大钱,我这点儿都不算啥。计划经济管理松散,经常多花钱。花冤枉钱的例子很多。有一回我们从美国进口了一个高桥电阻箱,用它鉴定能减小误差,是先进的精密仪器,好像花了四十几万。引进回来打开箱子一看,没有说明书,这也没有人会用啊。咱这边就向美方索要,美方赖账说合同上没要求配文件,不能给。要说明书可以得另行购买。结果又花32万买了一说明书。一个设备花双份钱不说,还耽误半年工期。这类上当受骗的事儿不少,反正也没人追究,花国家钱无所谓。
1978年到1980年代初国家政策的调整对我们也是有影响的。我去所里的时候是这么多年来对科研最宽松的时候。但80年后国家政策有大调整,当时也不知道,也理解不了,发生在身边的就是我们研究所规模要收缩,很多无谓的研究就被取消了。我们当时的很多研究是“小而全”的,不像现代社会有资源共享,可以采用先进国家的成果,当时的观点是保密的东西自己有总比用别人的强。比如我工作的设备是从法国进口模拟高空环境的,设备是亚洲第一,研究成果说有用真有用,关键是太费钱,就也被缩小了。80年代初开始“军转民”,企业要生产民品,要自给自足。我们之前是生活国家全供应,现在国家只给你一部分钱,自谋生路吧。80年就有点儿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思维,我们所也不知道能干点儿啥,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决定的,生产溜冰鞋。生产的东西质量根本不行,溜冰鞋的轮不是现在那种塑胶轮,都是用轴承做的,一滑哗啦哗啦响。所里人员也开始压缩,不再进人,人员也可以流动,想走的这时候可以走了。我们是保密机关,有几个上海的老先生,58年建所就在这儿,这么些年想回上海也回不去,孩子高中要毕业了,也只能每年探亲假时回去看看。
这比较松动的时候又让我赶上了。还是哪句话,“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弟妹、恋人都在哈尔滨,真想回家。也不是嫌弃四川地方不好,在那儿生活很好,工作、生活、饮食都还行。我还在后山找到了一片水塘,水塘边有块探出来的平滑石头,就是天然的跳台,我一空就去游泳,还能跳水。就我自己而言,那儿的生活是很惬意的。一星期保证看两个电影,《地雷战》《鲜花盛开的村庄》那些文革之前的电影都拿出了看,我们单位还有闭路电视,能看到美国电视剧《野鹅敢死队》,真不一样。我们看的新闻也不一样,比外界开放很多,国际国内大事都知道、我们所什么书都有,只要准许流通的书都有。让我一辈子在那儿搞科研也挺好。但是后代不能在那里,那里的教育水平只比山村强一点儿,教育水平落后到极点,在那儿安家肯定终生遗憾。老同志也都这么想,所以再苦也选择两地生活,把孩子留在家乡。
李宝琛很快就又一次踏上回哈尔滨的路,因为恋人在哈尔滨。而谈到自己的另一半,他的心情显然更愉快。他的恋人家庭背景在哈尔滨一度较为显赫,不过恋人的父亲在文革期间已经被迫害身亡。即使这样,在李宝琛看来,能跟这么一个出身高干家庭且品貌兼优的女性在一起,也是莫大的幸福。实际上,他能顺利回到哈尔滨,并得到一个不错的工作,他的岳母的确帮了很大忙,尽管老太太只是跟老同事简单说了一句话。同大多数人一样,在李宝琛这里,爱情的甜蜜是和家庭的幸福缠绕在一起的,这种生活的暖意附着在诸多关于琐碎细节的记忆上,所以显得很实在。
江油所的领导知道我想回家,找我谈话,问我想走么,想走就得结婚。要回去照顾父母这样的理由不好使,只有夫妻两地生活才是调动的先决条件。我就马上给家里发了带公章的电报,我的爱人就自己拿着电报去公社登记了。1980年元旦结婚,不到一年我就调回来了。当时要往回调得有接收单位才能迁走,要有接收函。当时我是技术员,有职称,去机关就把专业荒废了,没意思。我就去了哈尔滨市工业先进技术交流馆,技术协作办公室,只有这一个地方和技术有关系,负责信息技术交流。后来又经过几次调转到了现在的单位哈尔滨职工业余大学。从国家机关到了事业单位,2008年提前退休,退休金差1000多块钱呢。
李宝琛,出身于哈尔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祖上是满族镶黄旗,属于清八旗中的上三旗。1968年,他作为成千上万的下乡知青中的普通一员,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某建设兵团在黑龙江省黑河地区的一个马场培育种马。黑河离哈尔滨千里之遥,李宝琛很快就开始为回城做打算。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 27岁的李宝琛已经作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自动仪表专业读到了三年级。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他返城读书的历程尽管有点曲折,但总还是幸运和顺利的。
和我年龄相仿的人,这时候多数是下乡刚回来或者仍然呆在乡下,回城的途径基本上无外参军或招工,能上大学的人微乎其微啊。我这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68年下乡,在生产建设兵团1师11团,在黑河守边疆。那时咱们国家跟苏联关系紧张,我们这叫在“反修前哨”屯垦戍边。响应毛主席号召么,一方面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方面练兵。还是以农为主。我那时候在黑河马场主要负责培育黑河种马,也种地建房、上山伐木,工作还是比较出色。1973年以后开始招工农兵学员,那时我工作环境还不错,也没有什么上学的概念。参加了一次文化测试,因为工作紧张,有经营90多匹种马的任务(当时一匹两年的种马能卖四千八),测试完了也就算了,本来名额就少也没再争取。74、75年社会主要精神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我还代表团里去大寨参观学习。这前后我两次回哈尔滨探亲,第二次回家就感觉形势变化很大。最明显的就是文革的气氛没有了,人的思想也活跃了,都不那么保守了。那时知青返乡、上学的也活跃了、多了。自己感觉单在农村兵团工作不是长久之计。1975年开春我带着种马的血样去长春化验马四号啶,感觉长春那边形势更不一样了,社会风气、人的状态变化都特别大,社会思想好像不是我们当时主张的“扎根边疆”。就这么出来几次之后,感觉在当地就憋不住了,萌生了走的想法。简单的离开回城务工又感觉没意思,当时家里都在兵工厂当工人,回去分配也肯定在机械局,不想去,想当兵,还想上学。当兵的路不同,因为是团里的干部,团里不放就不能走。上学的路是通的,于是我75年就开始准备。
当时上学要经过文化测试、群众推荐,前两条都通过了还得单位保送。文化学习我心里是有底的,73年参加测试也不是很难,说得不好听就是看你认不认识字,加减乘除能不能算明白。我一直没间断学习。平时看马列著作,看毛泽东文集,社会科学书选。还有范文澜版的《论历史唯物主义》。再就是一些业务书,数学,主要是些简单的中学课本。我在团里是干部,除了能看着规定的一报两刊,还可以订《参考消息》、《解放军报》,这在当时可不太容易看到。我们属于部队系列,国内国际变化了解一些。有一些在军队搞情报工作的朋友就就给我讲苏、日军队的状况,当时中苏边境紧张,说苏联24小时可以从远东调7、8个师过来。那距离连飞机都要飞十几个小时,可见人家苏联的技术水平有多高。当时就想,无论是为了报效祖国还是今后自己发展,都要有文化。这就更坚定的想去上学。
后来文化测试语文数学都很简单,“群众推荐”我们一共是63个人。我自己投给自己一票,我就是63票满票第一名。单位一共有三个名额,第一上大学,第二上中专,第三中专预备。我第一就上大学了。第一志愿报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第二志愿是大连海军指挥学校,现在叫大连舰艇学院。虽然志愿报的是这样,海军指挥学校倒是差点先上了。大连海军指挥学校有面试,因为总要出国远洋,要代表国家形象,仪表得端正,歪瓜裂枣的不能要。过来招生的老师待一天就走,他们就先看档案。当时我们这些干部的档案在团里,招生的能看到。很多战士的档案在营里,要一级一级的拿上来根本来不及。能看着的档案也没有多少,还真选上我了,让我当天务必赶到。我们马场距离120华里,我就开着农场的胶轮拖拉机,把斗摘了开车头,一小时能开20多里,赶到了,人家看我各项指标都合格,就是报的第二志愿,问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学校啊。其实我当时主要是想回家,上哈工大就能回哈尔滨了,父母在不远游么。就这样海军学校那边还是告诉我回去准备基本就能上了。可这事儿让陪同的参谋长听去了,他上下一运作,这名额就让他外甥给顶了。这都是后来知道的。6、7月份哈工大的正式通知下来,我就准备上工大了。也没啥遗憾,7年过去总算回家了。
上了大学的李宝琛是被更多的人羡慕的,毕竟与我们在很多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经常见到的轰轰烈烈的返城潮相比,更多的人的命运在这个大转折的时期多少显得有些沉寂,他们似乎总是“沉默的大多数”。而返城的李宝琛也有自己羡慕和钦佩的东西,这也是他喜欢自己的专业——哈工大自动化仪表专业——的理由。
羡慕我的人?那是相当多。我们全团上万人,73年到76年四年走了不过百十来人,77年恢复高考后又走了也不到一百人。多数人后来的去向我和几个出来的几乎都不知道。
上大学,选理科是想干点儿实事儿。在农场搞了很多年机械,农场有的机器都会使。本身也喜欢机械这一行,也羡慕工人。大学里所学专业以前都是直接安排的,也不能自主选择。我学的专业是自动仪表专业。当时对仪表的感觉就是小表,男同志就学个小表好像施展不开,没有机械有意思。等开始学习了发现这仪表可不是“小表”,大的像楼房一样大。仪表老说法叫“热工仪表”,温度、压力、流量,凡是需要仪表测量的元素都需要仪表,现在航天设备也离不开仪表。
刚接触课程的时候跃跃欲试,先学制图、英语、高等数学。我们一个班年龄差别很大,从49年的到57年的,文化水平什么样都有。补数学时从初高中补起,开始还行,越往上越难。学一个学期后就基本把英语放弃了,学不过来。哈工大的教学比较正规,按国家安排有实践环节,三年级专业刚入门,连个正规图工都算不上就下去实习了。先去大庆化工厂、炼油厂,干的活儿是检修测绘仪表,主要是跟老师干,边干活边学习。我们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理论都说不上充实,更谈不上实践。仪表检修测绘还是比当地的工人强,手法上学的东西还是有效果的。在大庆干了三个月觉得学的东西有用,全是我们专业的必须知识。一天弄得跟工人一样,也说不上苦,感觉自己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充实了,挺高兴。之后又去大连仪表厂实习3个月,对理论学习有很大帮助,回头再学习发现数学、物理这些更有用。就彻底放弃英语了。当时我们学樊英川版的《高等数学》还学苏联的。
当时年龄比较大了,入学时24岁,78年毕业就28岁了。当时想一定要好好学习,为自己以后也好,为投身国家建设也好,都要好好学。我们当时都是这个心态。全班都统一起来,利用政治学习时间补课。每周六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我们有同学在门口、楼道把风儿,拿报纸在前面做做样子,没检查的就开始学习。我们把老师请来,门一关,让老师解题,一直到晚上九点,坚持到毕业。工大的老师真都是好老师,特别认真。文革过去了很多被打倒的老师都回到学校,但身体都不行,上一会儿就累了,讲的知识不会错,你问个问题他们有时候反应不过来,文革时候都被打傻了。那时候我们班老师都愿意来,能正经讲课,学生也认真听,能提出问题。我们这些学生年龄都比较大了,多数在农场工作过,基本都抽烟,老师想不起来了我们就给老师点根烟,边抽烟边想,有时候抽一半想起来就马上讲,要是一根烟抽没了就下节课讲,我们有位老师,平时在走廊在食堂在什么地方碰着他了,他马上就给你讲明白。很多老师现在都去世了,很多都对国家有特殊贡献。
1978年,大学毕业的李宝琛被分配到三机部在四川江油的一个研究所。又一次远离家乡,去那个陌生而僻远的地方,如今那个城市因为一次震惊世界的大地震而人所皆知。李宝琛在那里呆了两年,但正是在这里,他慢慢接触到经济转型这个时代命题的枝枝叶叶,也留下了一些属于他自己的美好记忆。
我上学的时候是“戴帽分配”,上学就定了你是给哪儿培养的,毕业就得去。我该去的单位是第三机械部航空工业部。毕业时候政策就变化了,赶上小平同志复出,说现在的毕业生不能浪费。这一个“不能浪费”我就被分配到四川江油624研究所,就是08年四川地震那地方。当时国家政策就是这个政策,要服从分配,虽然比较恋家,让去也就去了。我们就二十几个人,好一些的分配到北京机械局,现在都成了领导干部,还有分配到四川绵竹去搞科研,现在还在那儿,地震都赶上了。
当时还不知道去了让干什么,就想无论让干什么都好好干,结果第二天就被领到操作台前。设备是国家二级、省一级标准。买回来以后就没有人用,这个活是好汉子不愿干,坏汉子干不了的活儿。调整计量标准属于科研二线,后勤保障,不算一线,操作精密设备还不是谁都能干。当时我们去的都是清华、交大、哈工大这些好大学的学生,都在大山里呆着。我就分到这么一个工作,接手后我才知道,由于10年动乱咱国家10年没和国际上调试对标,所有的研究数据都是在标准错误的情况下得出的,都不能用。这时我们所里就比较重视计量标准,靠我的设备校准其他设备。我的设备马上就投入使用了,这就为所节省了一万两千多块钱。之前每个月都得拉着设备去成都校准一次,一次连去带回来最快一星期,我这个设备拿走了其他设备也得停工,这不是误工么。现在,我的设备定期拿到成都或者北京上海校准就行了,不耽误生产。
有没有奖金?肯定是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省了花了都是公家的,我这成果报到所里没人当回事儿。一万二不算多,那时我们地区的研究所一年国家有1600万科研经费,跟现在一两个亿差不多,我这点儿小钱儿,领导没看上。那个时候,四川是三类地区,工资少,大学毕业生一月45块钱,要在哈尔滨能赚66块钱。不过一个人足够了。每天就想着工作,也没别的要求,除了吃饭也没什么花销。个人工资哪能和国家科研经费比啊。
后来又有一个这样的事儿。第二年,我的设备需要一个配套设备,需要去上海买,大概一万八。我当时把计划报到所里,但没敢说多少钱,领导问我,我说挺贵的,大钱。领导就让我回去再各方面考察一下,是不是非买不可。过一段时间又开会,领导就问你那设备到底要不要,多少钱?我各方面都考察了的确是特别需要,不然很多工作都完成不了,就战战兢兢的说要花一万八去上海买,领导二话没说就批准了。我当时特别震惊。后来老人儿告诉我了,十万以上才叫大钱,我这点儿都不算啥。计划经济管理松散,经常多花钱。花冤枉钱的例子很多。有一回我们从美国进口了一个高桥电阻箱,用它鉴定能减小误差,是先进的精密仪器,好像花了四十几万。引进回来打开箱子一看,没有说明书,这也没有人会用啊。咱这边就向美方索要,美方赖账说合同上没要求配文件,不能给。要说明书可以得另行购买。结果又花32万买了一说明书。一个设备花双份钱不说,还耽误半年工期。这类上当受骗的事儿不少,反正也没人追究,花国家钱无所谓。
1978年到1980年代初国家政策的调整对我们也是有影响的。我去所里的时候是这么多年来对科研最宽松的时候。但80年后国家政策有大调整,当时也不知道,也理解不了,发生在身边的就是我们研究所规模要收缩,很多无谓的研究就被取消了。我们当时的很多研究是“小而全”的,不像现代社会有资源共享,可以采用先进国家的成果,当时的观点是保密的东西自己有总比用别人的强。比如我工作的设备是从法国进口模拟高空环境的,设备是亚洲第一,研究成果说有用真有用,关键是太费钱,就也被缩小了。80年代初开始“军转民”,企业要生产民品,要自给自足。我们之前是生活国家全供应,现在国家只给你一部分钱,自谋生路吧。80年就有点儿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思维,我们所也不知道能干点儿啥,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决定的,生产溜冰鞋。生产的东西质量根本不行,溜冰鞋的轮不是现在那种塑胶轮,都是用轴承做的,一滑哗啦哗啦响。所里人员也开始压缩,不再进人,人员也可以流动,想走的这时候可以走了。我们是保密机关,有几个上海的老先生,58年建所就在这儿,这么些年想回上海也回不去,孩子高中要毕业了,也只能每年探亲假时回去看看。
这比较松动的时候又让我赶上了。还是哪句话,“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弟妹、恋人都在哈尔滨,真想回家。也不是嫌弃四川地方不好,在那儿生活很好,工作、生活、饮食都还行。我还在后山找到了一片水塘,水塘边有块探出来的平滑石头,就是天然的跳台,我一空就去游泳,还能跳水。就我自己而言,那儿的生活是很惬意的。一星期保证看两个电影,《地雷战》《鲜花盛开的村庄》那些文革之前的电影都拿出了看,我们单位还有闭路电视,能看到美国电视剧《野鹅敢死队》,真不一样。我们看的新闻也不一样,比外界开放很多,国际国内大事都知道、我们所什么书都有,只要准许流通的书都有。让我一辈子在那儿搞科研也挺好。但是后代不能在那里,那里的教育水平只比山村强一点儿,教育水平落后到极点,在那儿安家肯定终生遗憾。老同志也都这么想,所以再苦也选择两地生活,把孩子留在家乡。
李宝琛很快就又一次踏上回哈尔滨的路,因为恋人在哈尔滨。而谈到自己的另一半,他的心情显然更愉快。他的恋人家庭背景在哈尔滨一度较为显赫,不过恋人的父亲在文革期间已经被迫害身亡。即使这样,在李宝琛看来,能跟这么一个出身高干家庭且品貌兼优的女性在一起,也是莫大的幸福。实际上,他能顺利回到哈尔滨,并得到一个不错的工作,他的岳母的确帮了很大忙,尽管老太太只是跟老同事简单说了一句话。同大多数人一样,在李宝琛这里,爱情的甜蜜是和家庭的幸福缠绕在一起的,这种生活的暖意附着在诸多关于琐碎细节的记忆上,所以显得很实在。
江油所的领导知道我想回家,找我谈话,问我想走么,想走就得结婚。要回去照顾父母这样的理由不好使,只有夫妻两地生活才是调动的先决条件。我就马上给家里发了带公章的电报,我的爱人就自己拿着电报去公社登记了。1980年元旦结婚,不到一年我就调回来了。当时要往回调得有接收单位才能迁走,要有接收函。当时我是技术员,有职称,去机关就把专业荒废了,没意思。我就去了哈尔滨市工业先进技术交流馆,技术协作办公室,只有这一个地方和技术有关系,负责信息技术交流。后来又经过几次调转到了现在的单位哈尔滨职工业余大学。从国家机关到了事业单位,2008年提前退休,退休金差1000多块钱呢。
我爱人的确是很优秀的。我们是77年经人介绍认识的,我可算是高攀了,她是干部子弟,在师范学校学英语。我家全家都是兵工厂的工人,标准的工人家庭,往上数还是贫农。我家邻居是我爱人父母的下属,说有这么一个好小伙儿,大学生。那边儿高干正好想找工人,经过十年浩劫,还是工人生活最平静、稳定,不受政治因素干扰。干部子弟也二十六七岁挑花眼了,看我还不错。刚确定关系我就去四川了。
当时不像现在,我们几乎没打过电话。当时要打电话很麻烦,要事先约好时间都去电话局,先登记说明要打电话去那儿,然后人家告诉你去几号台通话,接线员给接过去,还总断线。写信也不多,一工作起来什么都忘了,好几个月都不写信。我一到四川就给每个认识的人发了一封信,朋友、家人都一样:我已到,介绍一下当地情况,不用担心。然后就谁也不联系了,一心都在新设备上。现在家里想起来还说呢,那时候写信不超过五行,第五行还是:“一些都好,勿念”,就完事儿了。第一封信发出去了,两三个月再也没跟外界联系,我爱人以为这人出什么事儿了呢,天天在家哭,后来我岳母实在忍受不了,给我来了封长信一顿臭骂,我才想起很久没跟爱人联系了。后来我爱人就每来一封信提一堆问题,生活怎么样,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就拿着问题回答一遍再寄回去,当时通信主要是谈彼此的工作情况,很少像现在的年轻人又想又爱的。
79年1月份我回家探亲,刚离家四个月,具体部门没意见,上面组织部不给假,正常探亲是一年一次,每次半个月,规定是有妻探妻、无妻探父母、父母不在探出生地。我这些都在哈尔滨就回来了。当时带了几筐四川小橘子,竹筐是当地农民手工编的,橘子是当地特产。回哈尔滨来大家都没见过,可成了稀罕物了,都拿着玩儿不舍得吃。还带了当地的白酒“绵竹大曲”。我岳母拿了一瓶去工会给这些老干部喝了,单位老同志喝完以后都哇哇大叫,说这是什么酒,哪来的,好喝啊。我岳母说是准女婿从四川带来的,老同志们说给他写信,再寄点儿回来。这下可沾包儿了,我第二次探亲带了两箱“绵竹大曲”每箱24瓶,花了一个多月的工资啊。
1980年元旦结婚,当时我家不富裕,为娶媳妇我妈特意向我舅舅借了300块钱当彩礼,当时家里弟妹多拿不出一点儿闲钱。元旦结婚以后回家,去照相馆照结婚照,其实就是一张合影。我岳母家条件不错,给我爱人做了一件B级中山装,毛料的。我没衣服啊,就借来我弟弟为结婚做的大衣,不太合身,里面多穿了件毛衣总算撑起来,这么照的相片。我们领导很有人情味,过年加上婚假都快结束时,单位给我发来了一封电报,指令采购物品。过年商店、工厂都不开门,只能年后去,新年假期结束了我又在家多呆了一星期。我爱人是中学老师,80年放暑假她去四川看我。我们领导人特别通情达理,他就派我去成都出差,开了介绍信,这样我一个人的来回路费、住宿都不用自己花钱了。我就带着爱人去成都玩儿。还有个挺好玩儿的事儿,我爱人性子急,我俩赶火车她自己急急忙忙的往前走,我就看着她自己在前面,边走边从兜里拿出一块糖,剥好了往后一塞,正好塞到后面一个不认识的小伙子面前,给那小伙儿吓得转身就跑。我爱人举了半天没人接,挺生气的回过头,看人家小伙一脸尴尬的跑了,我在后面嘿嘿笑呢。上了车那小伙就坐我俩对面,我爱人一路都没好意思说话。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本网站链接:http://www.cul-studies.com